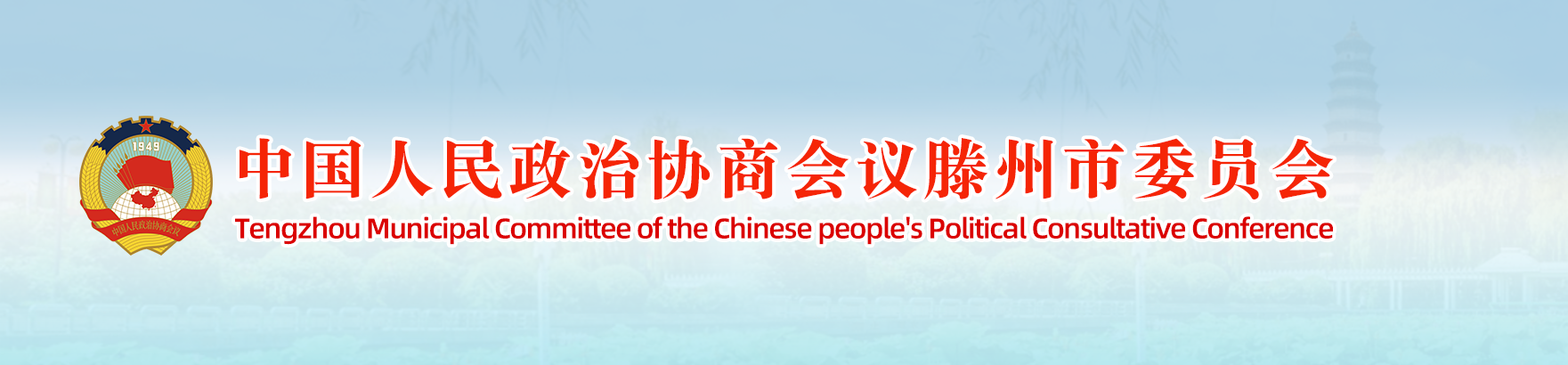
杨列敏
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叶嘉莹先生历尽磨难从不气馁,“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只因中华古典诗词涵养了她最美的“弱德”。
北平与台湾: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
叶先生本姓叶赫那拉氏,祖父乃前清进士,父亲是北大出身,然而少年初立就开始担负起人生的重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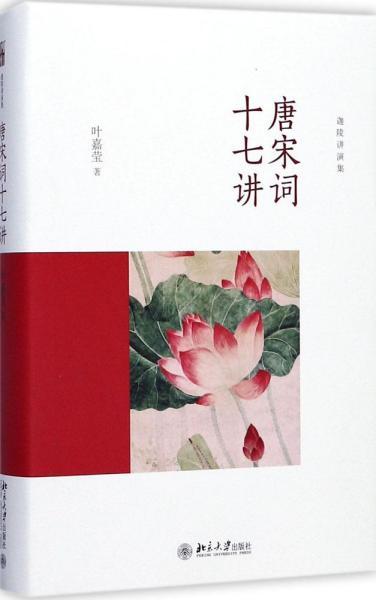
时值抗战,父亲转调后方,北平只剩下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作为家中的长女,叶先生不仅要照顾多病的母亲,自已读书上学,还要兼起家长的责任,教导和照顾弟弟。每天煮饭、缝衣,整个中学都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仅有的布料也留给了小弟缝制新衣。母亲去世时,她连一句知心话都未能向母亲诉说就已然天人永隔。但正是在那战乱的年代,在那样贫瘠的物质生活中,她开启了对古典诗歌的追寻之门。顾随先生的循循善诱、同学之间的真诚友谊,带给她生命的慰藉和希望。她的天赋就像深埋在土地的种子,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温度,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养分,也坚强地萌生,不可思议地发芽和成长起来。
然而现实的残酷,政治的动荡不安给她带来的伤害并没有就此结束。1948 年11月,因国内情势变化,叶先生随丈夫去了台湾。1949 年,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天,叶先生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同其他6位任教学校的老师,也一起因白色恐怖被捕。其后不久,她虽幸获释放,却失去了教职与宿舍,只能携带怀中幼女投亲靠友。白天,她怀抱幼女为营救丈夫在烈日下四处奔走;晚间等亲戚全家安睡后,她才能在走廊搭一个地铺带着孩子休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转蓬》)”就是她在“天风海雨”中发出的“幽咽怨断之音”。
美国与加拿大:芳根暂向异乡生,月明一片露华凝。
42 岁,对于叶先生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初到北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需要养育,八十多岁的老父亲需要供养,丈夫多病不能工作。全家的日用支出全部靠她一个人,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四处去找工作。刚刚接受哈佛邀请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她,甚至都不会英语,面对北美的学生,她必须学会用英文讲课。这样,已经人到中年的她,不得不每个白天努力操持家务,尽一个主妇所能做的一切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照顾每一个人。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家人都熟睡的时候,才找到空闲努力补习自己的英文课程,没有老师,一切只能靠自己,每天要查英语单词到凌晨两三点钟。哈佛燕京图书馆为她的勤奋刻苦所感动,特意给了她一把钥匙,使她能在闭馆后继续研读,有时当她在夜晚走过两侧列满书架的长长黑暗通道时,她竟会有一种古圣先贤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左右的感觉。
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叶先生已经可以用英文流利地讲述中国文学,后被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聘用。然而“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上天似乎总是要尽其所能地用磨难来考验这样一个女子。1976年,她总算辛苦地等到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成家,可是大女儿刚刚结婚不久,就和丈夫在一次出行中遭遇车祸,双双罹难。这次打击对她来说是更致命的,人到老年却遭受丧女之痛,命运之神似乎准备好了所有的手段要摧毁她似的。叶先生只有强忍悲痛地处理他们的丧事,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避免和所有人往来,几十天一个人待着,努力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她所有的安慰都来自诗歌也只能寻求诗歌来排遣这山一样巨大的悲痛和打击。
叶先生说:“我之为人,我之做事,不追求身体上的现实的一切享受。我不要故命清高,而是天生下来我就不在乎。我穿的衣服很简单,吃的东西很简单,我不觉得很怎么样。而且大家也奇怪,我怎么经受这么多苦难而居然活过来了,就因为我真的是在一切的压力之下,我不是斗争、反抗,而是承受,坚持。”
南开与中国: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1979年,叶先生向中国政府提出回国讲学的申请得到批准。40多年来,叶先生应邀到北大、南开、津大、南大、复旦等几十所大学讲学,她的足迹遍布祖国大陆的角角落落,最终“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
彼时南开大学许多教学楼被地震损毁还没有修缮完工,操场上林立着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叶先生每周讲授两次汉魏南北朝诗,地点在一间可容纳约300人的大阶梯教室。讲课开始后,同学们反响极为热烈,许多天津其他院校的学生也慕名而来,需要临时增加许多课桌椅,以至于开讲前叶先生要走进教室、步上讲台都十分困难。凡是听过叶先生讲课的,无不对她那热情洋溢、神采飞扬的独特魅力难以忘怀,无论汉诗还是宋词,其中的每一个字,都随着她清朗饱满的独特吟诵,荡漾在教室里,余音绕梁,袅袅不绝。现如今,南开年轻学子的热情尤胜当年。在她的讲座中,过道里、讲台前仍然是被挤得水泄不通。窗外星斗满天,室内灯火通明,台上与台下一同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
叶先生虽然是一位纤弱的淑女,但有着超过一般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承担悲苦的旷达与追求美好的执著。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包含的千姿百态的生命和哀、乐、忧、喜的万种情感深深地吸引了她,她说:“我余生之情感所系,就只剩下了诗词讲授之传承的一个支撑点。……我曾经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的话,其实那不仅是为了‘报国’,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
佛教传说中有一种神鸟,叫迦陵鸟。传说它生于雪山之上,美妙歌声能响彻三界,感动万物;听者常常陶醉其间,不能自已。叶先生一生何尝不似一只迦陵鸟,一世多艰,从未停止歌唱;辗转流离,苦难中诗词相伴,那其中的弱德之美,也只有她自己懂得。她把歌声传给身边的人,用尽自己的力量歌唱,令大家也能被这歌声打动和感发。
“一世飘零感不禁,重来花底自沉吟。纵教精力逐年减,未减归来老骥心。”无论命运的风雨如何,叶先生始终怀着一颗简单的诗心,看淡人生的起起伏伏,超脱凡尘的得失悲喜,致力于中华诗词的传承,使人生的道德境界得以升华,把自己活成一首隽永深刻的诗。
荐书人:杨列敏,滕州市政协委员、滕州市第一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