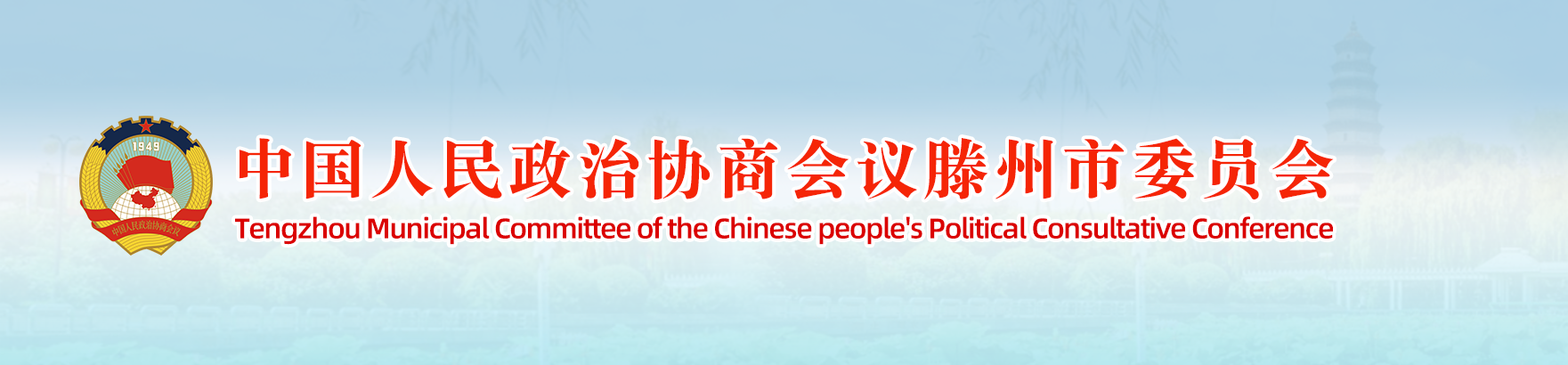
人生如逆旅 担尽古今愁
——从精神分析理论看苏东坡的苦与乐
赵 燕
提起苏东坡,你一定会想起他千里婵娟的高蹈浪漫、大江东去的超迈豪情、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乐观、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寂清冷;又或者,你会钟情于《凌虚台记》里他对上司不留情面的直言快语,《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想当然耳”的俏皮可爱,《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的文脉里流淌着的以长江大河而泻湖海停蓄的雄辩滔滔……

光明磊落的苏东坡、忠君爱民的苏东坡、豁达洒脱的苏东坡、才气纵横的苏东坡、人见人爱的苏东坡……一千个读者可能会有一万个苏东坡。李一冰先生的忧患著作《苏东坡新传》,带我们读诗、读史、读事、读人,分析透辟,字字珠玑,常有惊人之语开蒙心智,亦有深情厚意戳人心魂。这是记录苏东坡最好看的书,窃以为!
曾与好友一起讨论,东坡究竟是苦是乐?答曰:“实苦!他的乐是为了掩饰他的苦!”这一说法通透睿智,且直接采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A是对B的防御(也叫掩饰)”这一公式,也即苏东坡的“快乐”是对他“悲伤”的掩饰,快乐只是表象,悲伤才是现实。通观全书,这个解读不失为中恳之论。
是书于二十年前就已问世,今方读,是为憾;今能读,是为幸!曾经,基于对苏东坡的轮廓性了解,我肤浅地认为,乐观的品性是长在东坡血液里的基因,困境中的快乐是他的性灵自觉和自然选择。祖父苏序豪侠仗义,苏轼继承之,这是先天因素。在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之作《贾谊论》中,苏轼对贾谊志大量小、不能隐忍的表现颇有微词:“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文章充溢着志达智强的热血情怀和志存高远的淑世精神,其时,轼年21岁。1078年,42岁的东坡与参寥放舟百步洪下投入急流,他不禁感慨道:“人生千灾百劫,总要过去,只要此心无所执着,造物也奈何我们不了。”此等胸襟,注定他在苦难的锤炼里会越发强大。机械僵化的理由加上刻舟求剑的思维,更有那些绝世而立、光耀千古的文字,让我沉醉于他营造的美感与哲思中,任由自己的酷爱泛滥泼洒,把东坡的生活想象成了一幅幅闲情逸兴的图画,满眼风趣,满怀风雅。何曾深察过他现实生活中的蹇顿困窘?黄州衣食无着苦力躬耕、惠州瘴疠肆虐无医无药、儋州食芋饮水陵暴飓雾……
英雄不是瞬间诞生的,苏东坡也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无妄之灾来临时,处境的落差和对未知的恐惧,使他终日惶惶,“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残酷的政治迫害让他的心灵血流不止,数次几寻短见。来到黄州,寄居寺院,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一时难以救赎。而他又时时不舍曾经的亲朋密友,小宇宙热情的电波频频发散,却杳然无音,其境如斯:“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精神分析中有个小故事:若把一个人扔在孤岛,给他两个选择:一是独行,二是与仇人同行。大多数人会选择方案二,那是因为,坏的关系也胜过没有关系。苏东坡这样一个乐与朋友分享分担的人、一个满眼皆是好人的人,历经背叛、历经磨难,被弃置于状如真空的环境里,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经过三年自我疗愈,1082年,《前赤壁赋》诞生,形式是主客问答,内容何不是东坡挣扎超越的外化?逝者如斯,唯江上风、山间月,怡我情,悦我心,以主说客,自我抽离,自我解脱,让我们见证了苏东坡开释能力的强大。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创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把“自恋”与“力必多”平行对举(此二者与“攻击性”“关系”,并称为精神分析的四个轮子),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健康程度,取决于理想自我与本来自我之间的关系。两者相互冲突时,自恋就是不健康的、恶性的、低自尊的;彼此和谐相融时,自恋就是健康的、自信的,就不会感觉孤独抑郁。一眼即知,苏东坡选择成为了后者。《前赤壁赋》中主与客思想交锋的过程,就是拉进理想自我与本来自我距离的过程,是化解矛盾冲突使之趋于和谐的过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此时无主无客,只有物我、物物之间的情感链接。将天下藏于天下,将自己藏于天下,物与我都是“无尽藏”中的一分子,宠辱皆忘,无得无丧,通达澄明。自此,苏东坡烟雨任平生、无可无不可的人格底色浓墨重彩地激荡开来,自黄州,漫九州。
苏轼一生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漂泊中,不论有多难,他都热爱生命,主动寻求纾解消弥之道,像搜寻治病药方一样勤勉不辍。精神分析思想家比昂认为,面对挫折时,是抑郁、逃避,还是用思想使之缓解、容易接受?思考的过程,比昂命名为阿尔法功能。一个阿尔法功能强大的人,能将不能忍受的贝塔情绪(情绪B)转化为容易忍受的阿尔法情绪(情绪A)。苏东坡多梦,凭借着超凡的记忆力,他从不混混沌沌放弃解读自己潜意识的机会。梦是潜意识的表达,一个痛苦的体验经过阿尔法功能的作用,能将分裂的碎片融合为完整的梦的意象;一个自我功能破碎的人是不会做梦的,梦是缺憾的补偿、是愿望的达成、是情绪的释放。故而,苏东坡在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的神异梦幻,正是他心灵空虚、无所附着的精神皈依。梦多,是苏东坡阿尔法功能强大的表现之一,他善于把日间景与夜间梦结合起来,通过感受、解构、分析、梳理,让自己的潜意识被意识化,做梦解梦无疑成为他化解困惑、调解情绪的一剂良药。
情绪A战胜了情绪B,统一为情绪A,他把快乐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成了他颠沛流离一生的人间日常。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美酒美食、禅宗瑜珈……既是他力必多的外化,也是他攻击性的升华。无论身处何境,他都能创造出别样的活着的滋味,他把“活着”这门专业学到了极致,我们爱的,正是他健康自恋的充分表达。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遇挫,反弹;更挫,更弹,挫折的基石越垒越厚,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沧桑岁月馈赠给我们一位世无其二的人之仙者苏东坡。
书中一个情节让我久久难忘,苏轼从贬所返京的路上,陷害苏东坡的恶人之一章惇遭了报应,被贬往雷州,其子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苏轼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但因政治立场歧异,早与师门断交。风闻苏轼将回朝拜相,章援恐惧其回手报复(这真是以小人之人度君子之腹),耻于谒见,又不得不作垂死一搏,思忖再三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苏轼读后夸赞“这文字,司马子长(迁)之流也!”心里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彼时,章惇百计陷害的恶毒,章援背叛师门的伤痛,都被他抛到了九宵云外,仍认他们一个是多年老友、一个是得意门生,在体力不支的弥留之际复信并附白术药方,这是分享给章惇的养生之道。读来不由深恨他不长记性的那份善良,作者也不禁感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东坡德厚无疆、含弘光大,正是因为自己内心光明坦荡,投射到外界才是一片日月清朗,方可上陪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儿,悠游于各种客体关系之中,并在其间得到最大滋养。
何以他人眼中的苏东坡没有李一冰先生笔下这样厚重丰满感人至深?李一冰的主责主业本是经济学,惜于国破家毁之际,遭贪佞构陷,渡牢狱之劫,身无以安,命无以立,被迫转入文史研究书写。狼狈之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的苏东坡,正是作者半生忧患的真实经历;文中那些对政治局面的分析和对小人深入骨髓的描摹,皆是自己的切肤之痛,化作他乱世中的无奈与愤慨,投射于东坡,投射于是书。韩愈在为柳宗元作墓志铭时说到,倘柳宗元贬谪时间太短,终究出人头地,则如此文学辞章,想必未能特加着力,作品也就肯定无法留传后世。一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情有郁结,无道可通,寄于文字,是借东坡形骸浇一冰之块垒也,所立之言终成不朽!人生得失,难以短暂时光看待,其屈辱悲痛,当时哭之恨之,放眼量去,祸福得失,亦难遽断。
苏东坡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燃起文化的思想火炬。古邑滕州,也曾泽被过他的光芒。元丰元年七月,时任徐州知州的苏东坡莅临滕县视察,为我们留下了文章《滕县公堂记》、诗歌《滕县时同年西园》、水墨画《筇竹图》,可惜无论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还是李一冰先生的这本新传,都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更详尽叙述,实为憾事!滕州作为助苏东坡成为温润如玉君子历程中的一粒沙石,磨练、雕琢了他的人生,滕州何其有幸!承载着追慕东坡遗风的集体意识,我们与这位可爱的老头儿有过这样近距离的勾连融合,作为滕州人民,又何其有幸!
东坡已矣!精神永存!东坡精神已成为我们烦恼时的趣、困境中的力、暗淡处的光。人生如逆旅,担尽古今愁,踏平坎坷,笑对人生,心中有东坡先生一路同行,足矣!
作者:赵燕,市政协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