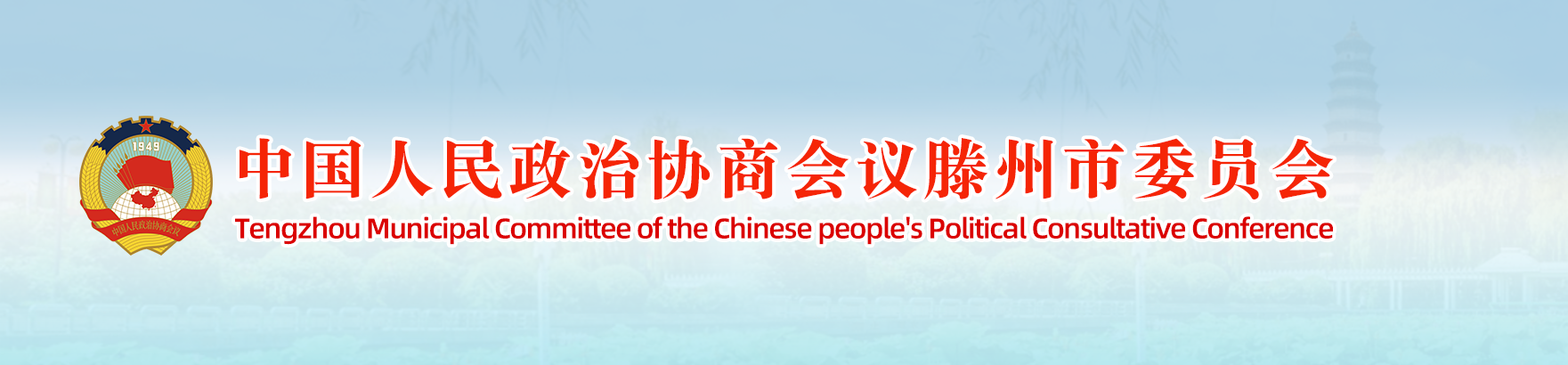
美兮灵犀弦外音
——读《枕上诗书》偶感
赵 燕
起至诗经,兴至唐宋,脍炙人口的古诗词云蒸霞蔚、五彩缤纷,张口即诵的篇章里,背后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蕴含着多少揣测难明的情感?一则诗文,或可脱离险境,或得成全美意,无论是单寄表心迹,还是与君相酬答,是美的创造,是宽解包容,更是灵犀间的懂得。读《枕上诗书》数篇,不由叹曰:弦歌之外,雅意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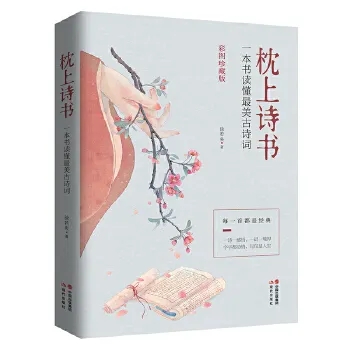
还记得张籍的《节妇吟》吗?“恨不相逢未嫁时”,何其熟悉?又何其深情?全诗云: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错的时候遇见对的你,却不得不错过,刻骨的抱憾,饱含万千不舍,道出多少痴情儿女的隐恨,倾心流淌的情感无处安放,关系再无转圜之机,只能就此别过,相忘于江湖……世人感慨系之咏叹此情者颇多。然,诗人初心何解?是“不得不”的错过吗?诗名全称为《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可知其意旨无关爱情。晚唐中后期,李师道欲拉拢文人官员以壮己力,时为太常寺太祝的张籍位列“正面清单”之中。张籍深知,在政治棋局动荡的大盘里,多少文人因站错队伍,落了个万劫不复,守忠义全身退,究竟如何抉择?他深知,恩师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劝阻董邵南投靠藩镇,其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立场不言自明,若依附李师道,那便是辱没师门,日后怎得复见?夜寂寂,月朦朦,难眠长安城;风凄凄,灯烁烁,愁肠千转意难平……时下张籍眼患重疾,但心中火未熄、光朗照,屈原不是常以香草美人以明其志吗?何不假以他人之口以寓己心。三思而后,他以女子纠缠彷徨之境中的立场婉拒了李师道的招揽。“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看似心性不定、余情未了,恰是张籍希望李师道能读出自己内心撕扯和分裂的痛苦,以期获得李的谅解宽恕。拒绝是一件难事,需要内定力、大智慧、巧思谋,又何况被拒者有杀伐决断之能、左右时局之势,一言一行皆需小心翼翼、不露破绽。李师道收信,读懂来意,不再为难张籍。后,李举兵叛乱被擒而身首异处;幸,张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一首好诗,可救人于危困,亦可解心上难题。
“行卷”是张籍时代盛行的取士方式,即主试官员除审阅试卷外,还可参考考生平时作品决定是否录用,在朝中有地位的人与主试官相识也可引荐人才。朱庆余曾得张籍赏识,而张籍也乐于荐拔后辈,二人珠联璧合、惺惺相惜,又恰恰符合体制机制的设置条件,实乃幸事!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透过诗句,仿佛能看见新娘脸上泛起的微微红晕,听到她在夫君耳旁的娇嗔低语,画面感十足。这首《近试上张水部》是诗人朱庆余临近科举考试时,因担忧文章欠佳写就,目的是向张籍讨个准信儿。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朱庆余以“洞房花烛夜”暗指“金榜题名时”,他为新妇,张籍为夫君,主考官是公婆,“画眉深浅入时无”实为朱庆余对张籍的询问。张藉读后回诗《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越州采菱女,面若芙蓉,美艳动人,却仍怀疑自己不够美。明知很美仍然求证,是内心不够自信?是忐忑前途未卜?还是为追求确定之后的自恋满足?揣度朱庆余当时之心,大概不出上述之意。“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虽然齐地产贵重丝绸,却并不值得看重。采菱女天籁般的歌声,才敌过万金之贵。张籍以采菱女喻指来自越州的朱庆余——你放心!汝之文采非凡,出类拔萃,不必担忧!二人问答,别出心裁,若非心意相通,外人岂可领会?!
有些心思终究无法直白表达,张籍的故事便可见文字寄怀的妙处。但若二人心意相左,或虽其心一兮,只因信息不对称,会错来意,酿成悲情故事者也有其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便属此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是“寻春遇艳”的回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重寻不遇”的感伤。彼此期待,彼此爱恋,彼此思念,崔护却因功不成名不就错过期待、躲闪爱恋、辜负思念,桃园佳人相思成疾,误将物是人非的喟叹理解成星河永隔的绝笔而芳魂永逝,不亦叹乎!不是不念,不是不懂,只是心意的频道未曾交集,话说恋爱中女性智商为零甚至更低,该诗或亦可佐证。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枕上诗书》置于案头多日,初看始觉无趣,似乎只是诗词的普通赏析,过于浅白了些。想来,案上是劳形之地,读书必得于恬淡时、安详时、宁静时才可看出妙趣来。此书为长者所荐、贤者力推,必有可读之处。果然,端午假期一气读完,得此心得一篇,汗颜无甚新意,几无真知酌见,但《枕上诗书》确是好读书者寻访诗词背后故事的佳所,可消遣、可养心、可启智,开卷有益,此言不虚,本书值得一观!
作者:赵燕,市政协研究室

